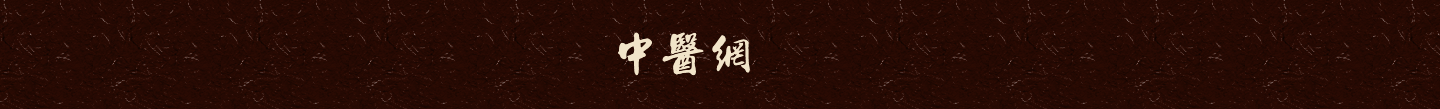韩南一位可作后世向导的学者节能
中医保健 2020年10月11日 浏览:3 次
韩南
韩南,美国中国文学研究家,欧美“中国明清小说研究第一人”。1927年1月4日生于新西兰。于奥克兰获西方文学硕士学位后,再入伦敦大学学习中文,195 年卒业。后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师。196 年赴美执教,先后任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副教授、教授。专攻中国古典小说和部分现代作家(如鲁迅、茅盾)。长于考证,兼用西方新批评、叙事学等研究方法,在《金瓶梅》话本小说和李渔研究中,成绩斐然,多所建树。著作有《中国白话小说》、《中国白话小说史》、《金瓶梅探源》、《李渔的独创》、《恨海:世纪之交的中国言情小说》等。2014年4月27日病逝于美国,享年87岁。
韩南教授在译文方面的贡献,虽没有霍克思(David Hawks)之译《石头记》和余国藩之译《西游记》这类“巨幅”的杰作,但他的文学造诣绝不亚于这两位大师,记得我读他释译的《无声戏》和《肉蒲团》,每每在深夜里击节赞赏。
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同事,也是美国汉学界我最敬仰的学者。他的本行是古典小说,而我的专业是现代文学,本来该是“隔行如隔山”,然而我和他的学术关系却特别密切,最近这两年在哈佛,甚至每隔一两个礼拜必聚会一次,共进午餐,我藉此也向他请教学问。去年秋季我开了一门晚清翻译小说的研究生讨论课,他竟主动前来旁听,于是我邀他主持几场讨论:从林琴南的《茶花女》到《迦茵小传》,从《昕夕闲谈》到福尔摩斯,他如数家珍,而且逐字逐句地推敲对照,使我这个粗枝大叶见林不见树的“学者”不胜汗颜。
韩南教授和我的半师徒关系(当然他不会承认的)源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时我被普林斯顿大学赶出门外,初到印地安那大学任教,正式从历史转人文学的领域,而系里人手不够,遂要我除了主授现代文学之外还要兼授古典小说。我在这方面从未受过正式训练,所以只好恶补,自己每天开夜车从唐传奇直读到“三言二拍”和《儒林外史》(《红楼梦》例外,以前读过,但仍要重读),但苦无良师,即使阅读其他学者的有关著作,仍觉不过瘾。遂想到向韩南教授请教。
当时我和韩南素不相识。在现代文学方面,我早已师从夏氏兄弟 夏济安和夏志清教授,又受业于捷克的普实克(J. Prusek)教授,在当年可谓得天独厚。然而在古典文学方面,我却不敢在志清师前献丑,甚至写了一篇关于《老残游记》的论文都不敢寄给他看。恰好我看“三言二拍”着了迷,对于“说书者”的角色还是搞不通,于是斗胆写信给韩南教授请教,并且问及他对于某些学者论点的看法。不料他马上回信,有问必答,而且言简意赅,因此我们就断断续续通起信来。似乎过了不久,他就寄来他刚在《哈佛学报》发表的两篇关于鲁迅小说技巧的长文。我那时已经在研究鲁迅,但在分析鲁迅小说的艺术技巧方面仍不得要领,读了韩南教授的文章后,我吓出一身冷汗!这本非他的“专业”,然而他下的功力之深,却远超过我这个“鲁迅专家”!譬如他考证鲁迅小说和东欧文学的关系,竟然把果戈理、安特烈夫和显克维支的作品研究得十分透彻,然后逐篇推敲,并与鲁迅的小说比较,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把我的旧稿丢掉重写,多年后才出书,寄了一本给韩南教授,心中却十分不安,因我的方法毕竟和他不同,不知道他是否喜欢。
不料我们却因为鲁迅结了缘。后来我才知道,他除了鲁迅之外,对于老舍的研究也下了不少工夫,甚至对五四文学各大家都有他的看法(例如茅盾的短篇小说更值得读),而且也指导过现代文学的研究生。换言之,韩南教授非但对现代文学不歧视 当年的汉学家大多如此 而且还颇有研究,因此我更佩服他。后来夏志清教授退休,哥大为他举行宴会,韩南教授特地赶来参加,夏先生对韩南教授也另眼相看,甚至公开宣布除他之外韩南教授乃天下第一。韩南教授一向腼腆,虚怀若谷到了极点,我不知他当时如何感受,但却认为夏先生的评价极为中肯,事实上,韩南教授的泰斗地位在美国早已得到公认,他的著作屡屡获奖(他的《李渔的独创》The Invention of Li Yu一书就得过“亚洲学会”的最佳著作奖),他的桃李满天下,所以当年前他自己退休时,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回来了,大家济济一堂开学术会议,韩南教授一贯其谦虚的作风,在会上不作讲评人,却自愿和学生在一起,提交一篇论文,“新小说前的新小说”,当时我听来真是前所未闻,因为他独排众议,把梁启超的新小说“鼻祖”的地位降低了一点,也把晚清新小说的起源提前了几年,甚至提出行家从未听过的一个传教士的名字 傅兰雅(John Fryer),据他后来亲自告诉我,曾到加州柏克莱的图书馆检阅傅兰雅的档案多次,而我个人本是学近代史出身,却不知道傅兰雅在1896年离开中国后就担任加州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的教授。
韩南教授对于这些传教士也没有偏见,只要是和他研究的题目有关,他必不分中外古今,上穷碧落下黄泉,到处求索考证。他为了探讨中国第一篇翻译小说《昕夕闲谈》和原著,就不知下了多少工夫,甚至从浩如烟海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去找,当然也免不了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图书馆数次,最后还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他从中文译名的“昕夕”二字悟出来原著小说的英文名“Night and Morning”,原来是英国政治家Bulwer Lytton的小说巨作。多年悬案,终于得到解决。
我和韩南教授的定期午餐,不仅得益于他在研究上的经验,而且因为我对晚清的翻译越来越感兴趣,研究的范围也和他愈来愈接近,真的变成同行,互相切磋学问,其乐也无穷。令我汗颜的是:每次我以为自己有所发现,向他说起,原来他早已解决了,而没有解决的问题仍是悬案,他正在研究中,譬如清末小说《电术奇谈》到底是周桂笙译自日文原著?抑或是日文原著本身也是译自英国小说?韩南教授告诉我: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的研究,这位日本作者菊池幽芳是从一本在伦敦得过奖的英文小说译成日文的(周桂笙再转译成中文,吴趼人再加润饰),然而菊池虽然译过不少英国小说(如哈葛德的作品),但他自己也写过不少欧洲风味的小说,以假乱真,甚至他自己的一篇小说后人都以为是改译;而最妙的是,韩南教授经过仔细调查后才发现:原来这本《电术奇谈》是否原作,菊池自己也搞不清,在一处列为翻译,在另一处则列为他自己的作品。
因此我从这个个案悟到 也是韩南教授的看法 原来晚清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的过程,单因“信达雅”的方法来检视是行不通的。譬如他说:梁启超的《十五小豪杰》本来就是译自日文,而日文本又译自原本译自法文原著凡尔纳(Jules Verne)《两年假期》(Deux ans de vacances)的英译本!这一种“文本旅行”当时十分普遍,然而可以作后世“向导”的学者并不多,韩南是少数中的一位,事实上我还没有在美国看到任何学者在这方面下过如此深厚的工夫。[NextPage]
走笔至此,我非但为自己感到惭愧,也为中国的学者蒙羞,为什么“近代文学”的研究还挣脱不了语言的牢笼?懂中文却不懂日文,知英语却不解法语。另一方面,日本学者如樽本照雄花毕生精力编就一大册晚清书目,至今华裔学者无人可望其项背。中国学者除了苏州大学的范伯群教授和他的弟子们,似乎对于晚清民初的通俗文学 更遑论翻译小说 存有偏见,认为不登“新文学”大雅之堂,即使研究也未能及得上韩南教授的精密对于广告点击和广告位出租。他非但分析细致,而且非常注重版本,记得有一次我到上海图书馆查资料,恰好韩南教授也托另一位朋友为他查《昕夕闲谈》这本小说的第一版,我无意中经过陈建华的帮助在楼上古籍部找到了,欣喜若狂,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对韩南教授的教诲有所回报。后来我才知道:他对各种版本早已了如指掌,找出这个版本只不过要看看小说的结尾是否删掉而已,而我又粗心大意,影印时来不及查,回美后才发现果然是有缺页!
研究学问不可一蹴而就就必须与当地的企业取得合作关系。比如说餐饮业,必须一步一步地来,更不能好高骛远,动辄以理论唬人 这是我从韩南教授处学来的浅显道理。然而自己却不能身体力行,往往徘徊在理论和资料之间,两者都不够功夫。但令我最吃惊的是:韩南教授对于西方文学理论 特别是法国的“叙事学” 十分精通,却深藏不露,最近在讨论翻译理论时,他又不慌不忙地说:“我看了不少理论的书,觉得Gideon Toury的所谓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还有点道理,至少对晚清略有帮助。”我听后赶紧叫学生去找来研究讨论。后来我又向他请教描写早期上海的言情小说,他一口气提了好几本书名,我遂立即从图书馆借出来,但每次见面我又不好意思,因为至今我也只读过包天笑的《上海春秋》,还有吴趼人《上海游骖录》的部分,而韩南却自嘲地说:他看过的晚清小说太多了,情节混在一起,自己都记不清了!我不敢问他到底看了多少本,我猜至少也有几十本吧。记得去年年底离开剑桥返香港之前又和他见面,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本小说《毒蛇圈》,看来似乎又在作另一篇论文的研究了。
我不禁暗自叹道:他从《金瓶梅》作到《毒蛇圈》,又从《肉蒲团》的翻译研究到李提摩太摘译的贝拉米小说《回头看》,真正是事无巨细,到了韩南手中都成了“精品”。我还要指出的是:韩南教授中英文俱佳,这本不足为奇,但是许多汉学家英文写不好,而韩南的英文造诣则非等闲之辈可比,而且他文如其人,言简意赅,没有一句废话。据说他在看某一个学生论文的时候,不自觉地修改她的英文,而这位后来颇有名气的女学者,当时颇引以为忤,认为自己的英文不错,老师何必要改?我听后恨不得拿一篇自己的英文文章请他逐字逐句修正,如此才能真正学到一手好英文,可惜时不我与,自己也做了教授,同事之间相敬如宾,我每次要拜韩南为师,他都以为我在说笑,学英文的事当然也搁浅了。但我还是从他的英文译文中悟出不少心得。
韩南教授在译文方面的贡献,虽没有霍克思(David Hawks)之译《石头记》和余国藩之译《西游记》这类“巨幅”的杰作,但他的文学造诣绝不亚于这两位大师,记得我读他释译的《无声戏》和《肉蒲团》,每每在深夜里击节赞赏,时当1990年代初,韩南和杜维明教授请我先来哈佛客座,住在学生宿舍,半夜时隔邻传来派对音乐之声,我却独览《无声戏》和《肉蒲团》,时而看英文时而看中文,其乐无穷。《肉蒲团》是所谓的“ ”,是否李渔所作目前尚不得知,但原文似乎甚粗糙,远不及英文译文之令人莞尔,真是妙在不言中!韩南先生平日不苟言笑,不知他译《肉蒲团》时作何态度?我猜他一定和我一样,将这本“ ”作为“笑书”,从文字转译中得到无比的乐趣。这当然不足为外人道也,有心者可以和我一样,把中英文对照着看。除此之外,韩南教授译本的序言也是有名的言简意赅,但往往一语定江山,记得他在《无声戏》的译本篇首说过一句“名言”,我至今还约略记得:欧洲在17世纪初发明望远镜,不到卅年这件“奇物”就进入明朝小说的世界!原来是李渔笔下的那个穷书生竟然用望远镜偷窥邻居大家闺秀,最后竟然缔结良缘的故事。(故事题目我忘了,我看的是韩南的译本。)
所以当夏威夷大学出版社请我为韩南翻译的《恨海》作“评委”时,我不禁感到莫大的荣幸,当然赞不绝口,此书一出,大家不约而同都用为教材,但却没有留意韩南还连带发现了另一本小说《禽海石》,这本小说可能是最早公开提倡婚姻自由的清朝小说,而吴趼人反而保守,遂写了《恨海》与之对抗。我对这本译文唯一的批评是:前面的序文似乎太短,似乎意犹未尽,然而,这就是他为学的典型作风,一句废话不说,甚至我们认为是真知灼见的东西,他可能都认为是废话。这又使我想到不少中国学者,著书立说往往洋洋数十万言,但内中多少是研究成果?多少是废话?
(本文节选自李欧梵为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写的跋,原标题为《韩南教授的治学和为人》)。
(:王谦)
池州白癜风治疗医院有哪些开封治疗白癜风医院在哪
辽源看白癜风专科医院

- 上一篇: goq2incr节能
- 下一篇 巨蟹座72883周运势节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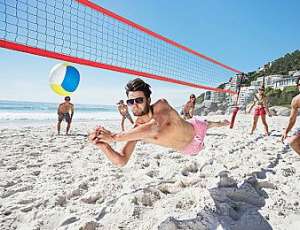
-
尤文黑了国米的冠军莫拉蒂有录像裁判就好了
2020-07-04

-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第六届膏方文化
2019-07-16

-
阳雀花根的功效与作用
2019-07-11

-
紫鹃试真心试出宝玉的痰证
2019-07-07

-
倒生莲的功效与作用
2019-07-07

-
介绍帮你暖手暖脚的食疗方法
2019-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