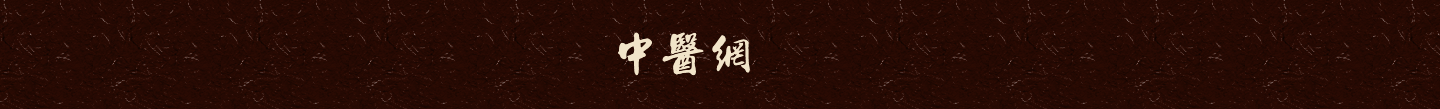藩国何伟从中国人的角度观察埃及
偏方秘方 2020年07月20日 浏览:3 次
何伟表示希望将来能住在中国
何伟说,他在美国的读者分两种:一种去过中国,对中国有所了解;还有一种知道他们的东西都从中国来,希望了解中国。 2011年,何伟(彼得·海斯勒)从美国回到中国,为他的《寻路中国》中文版做宣传,这是他在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书。那时何伟的知晓度仅限于很小的媒体圈,他的华裔妻子张彤禾因《打工女孩》的热销都比他出名。那时,他自己都觉得《寻路中国》应该没什么人会感兴趣,中国人怎么会对美国人写的工人农民感兴趣呢? 过去三年多里,何伟一家始终在埃及生活工作,但他在中国的知名度和读者数仍然都远甚于美国,虽然他关于中国的作品都是为美国读者写的。2014年9月初,何伟又回到了中国,去领取某时尚杂志颁给他的一个奖,还有排满10天的采访。何伟是,这些都能应付。9月7日,何伟在上海接受了早报的专访,这是第三次采访何伟,也是最轻松的一次,只谈这三年多他都在做什么。 三年里一直在开罗 基本没有回中国 2011年,何伟的《寻路中国》中文版出版,这位曾在中国工作、生活了10多年的美国人进入普通中国读者的视野。三年里,他在中国成了畅销书作家,有一大批忠实的年轻读者,尽管他所有的作品都用英文创作,目标读者是美国人。 在过去三年里,何伟在中国出版了三本书《寻路中国》、《江城》和《奇石》。当被问及三年里是否真的憋住没有回中国,他说只有在2012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公司的活动,借此回来了两三天。何伟说他主动避免回到中国,“因为在埃及工作很忙。”2010年,何伟离开美国来到开罗,在当地学阿拉伯语,学习埃及的文化和历史,采访政治运动和国家领导人,他要写一本关于埃及的书。“没有回中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不想让中文和阿原标题:法媒:空客A320失事是34年来法本土最严重空难拉伯语混起来。” 在开罗已经快4年,现在何伟已经能够用阿拉伯语跟埃及人日常交流,也能做简单采访,但如果采访很深入、复杂的话,还是需要翻译。“我老婆(张彤禾)的阿拉伯语比我好多了,她比我聪明。阿拉伯语没有中文难,难的是我还有两个4岁小孩要照顾。当年我学中文是在涪陵,我在那当老师,没有其他事情,业余时间比较多,就都用来学语言了。”他的双胞胎女儿也跟他们住在开罗,上当地的私立幼儿园,“在开罗,中上阶级埃及人都不去公立学校,因为公立学校特别差,这跟中国不一样。所以我两个女儿去的都是私立学校,学校语言是英语。有文化的埃及人,用的语言通常都是英语或法语。”何伟说他两个女儿都能适应开罗生活,也都懂阿拉伯语,“她们能听懂阿拉伯语,保姆是本地人,保姆对她们说阿拉伯语,但她们都用英语回答。”双胞胎暂时不会汉语,“我觉得这样挺好,我跟老婆用中文说些事情,她们就都不懂。” 想写一本观察埃及 历史、文化和现实的书 过去三四年里,何伟不定期地为《纽约客》写关于埃及的文章,追踪埃及诡异的政治变局,但这些不是何伟在埃及工作的重点。他在埃及居住生活,是为了写一本关于埃及的书,是像《甲骨文》(编注:未出版简体中文版)那样观察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的书。过去几年里,中东是国际的“富矿”,何伟可以不为所动只关心他要写的埃及,但何伟还是有点抱怨自己在过去4年里写的东西太多了,“写东西就有钱,不写就没收入。”甚至连何伟都有这样的苦恼。作为《纽约客》的特约撰稿人,他是29日下午进入淘汰赛没有底薪的,但好歹这是份稳定的工作,而且也适合自己去写书,“好的是,自由;不好的是,收入不稳定。但我明年要写书,他们可能会不太高兴,因为这样就不能为他们写东西了。”他的太太、《打工女孩》的作者张彤禾,现在是自由撰稿人,“她也想找一份稳定的媒体职位,适合写长文章或写书的工作,但现在媒体不景气,没那样的机会。” 在埃及已经快四年,刚刚完成前期研究工作,何伟打算明年开始动笔写。“我的书,一部分是关于埃及这几年的政治,更多是关于埃及的历史、文化,就像《甲骨文》写中国一样。”穆巴拉克下台,兄弟会上台又下台,将军塞西掌权……“在埃及,我看到的政治改变,已经够了。”去年何伟去参加了一场抗议塞西的游行,结果发生了枪击,在混乱中他把腿摔断了。何伟常会提到,有些国家、地区他不去,那些危险的地方也不会去,因为“我有小孩,可不想被抓” 。 在《奇石》中收入了2篇何伟观察埃及革命的文章,比如《广场上的清真寺》,写于何伟刚到开罗的时候。在这篇写于埃及革命之初的文章里,他几乎预言了埃及革命之后的戏剧性转变,“我对埃及革命是有很多个人疑问的,我所看到的不是革命,而是一个接一个的政变。革命是彻底的变化,但我没有看到。未来如何,我们还得继续观察。但我对埃及的未来并不乐观。” 何伟说他对埃及的民主比较悲观,“美国和西方国家,看到 革命 都是乐观和支持的。在他们看来,改变一个传统社会很简单,成为民主国家就可以。他们不知道,在一个传统社会,它自身会有很多问题,比如教育、经济、宗教等等。在伊拉克也是这样, 我们侵略伊拉克,因为它有一个独裁者,我们帮助他们推翻独裁者,过了一两年就好了。 他们想得太简单。大多数的美国领导人,他们只是看报纸了解那里,即便去这些国家也是短暂访问,他们不可能有那里长期居住的经验。” 计划中关于埃及的书类似于写中国的《甲骨文》,在埃及的这几年观察同样也得益于在中国的经验,“我自身有美国人的视野,但同时我在中国生活那么多年,当然也会有中国人的角度。我经常会跟彤禾讨论,如果是在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角度真的很重要。” 尽管用英语写作 可更多的读者在中国 何伟在美国出版了4本跟中国有关的书,从这4本书在美国的接受度变化,何伟看到的是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我写《江城》的时候是1998年,大多数的出版社不愿意出版。他们说,这本书是好的,但美国的读者对中国的小地方不感兴趣。但他们错了,这本书出版之后,在美国还是比较受欢迎的。现在有关中国的书很多,以前关于中国的书都是政治,没有其他,现在更丰富了。”何伟说他在美国的读者主要分两种,有一部分是去过中国,对中国有所了解;还有一些人,他们知道他们所有东西都是从中国来的,所以希望了解中国。“我老婆写《打工女孩》,很多人都去看,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用的东西是中国生产的,他们想了解那些制造这些产品的人。” 但何伟最多的读者还是在中国,“我也很惊讶那么多人读。《寻路中国》出版的时候,我原以为,只有我采访过的那些人才会对这本书感兴趣,普通中国人可能不感兴趣。一个外国人采访中国的工人、农民,我想他们会觉得没有意思。”何伟的作品在中国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何伟不希望美国读者在读了他的书后会有这样一个反应:还好我生活在美国。他不在书中取笑、歧视中国人,即便是他在书中的幽默也避免如此。 “幽默感特别重要,我第一本书《江城》出版后,给我的朋友艾伦看,他说, 我喜欢这本书,里面很幽默,我不知道这些幽默是否存在取笑中国人的成分。 但我的说,这些幽默很自然。我很高兴,中国读者能理解这些幽默。我在涪陵的时候,跟中国人说话特别喜欢开玩笑。所以我写涪陵,我会很自然开玩笑。在埃及也是如此,但我们看埃及,总觉得这是一个悲剧的地方。美国或欧洲看发展中国家,特别严肃,画面有太多悲伤的地方,我不喜欢这样一种呈现方式。” 何伟的中国,大都是普通人的故事,他计划中的埃及故事同样如此。在埃及,他写小人物,也写领导人。何伟即将发表的一篇关于埃及的文章,是一个清洁工的故事。“他是文盲,他很聪明,他是这个社区的垃圾清理工,他很了解哪个人扔什么垃圾,从垃圾知道这家人干什么。他经常告诉我,你扔掉的面包还是好的,我们昨天把它做成三明治吃掉了。”在埃及他也认识一些中国人,所以也会写一篇在埃及的中国人的文章。“在埃及,他们对中国人比较有好感。我曾到西奈半岛旅行,那里人靠走私赚了很多钱,他们有了钱就造宝塔样子的房子,他们说中国是个有钱的地方,他们学中国人有钱了造房子。” 回到中国可能 比在美国工作更重要 关于中国或者埃及,何伟的写作都是故事,他庆幸自己读的不是而是文学,“而且我读书的时候没想过要当,因为我的理想是写小说,但是我对社会很感兴趣。我很高兴,没有在大学里学过,我在大学读小说,也采访很多人。”其实在大学的时候,他写了很多小说,但觉得写得不好。“实际上我写小说的时候特别严肃,我会想要跟海明威他们一样。但是我的非虚构写作就特别自然,有特别自然的幽默感。所以现在也没必要去写小说了,我在埃及的经验足够有意思,没必要去虚构。如果我受伤了,不能走路不能采访了,那我会去写小说。”个性上,何伟更喜欢跟人聊,更喜欢去发现新的事物,“小说里要写 亲爱的 ,我可说不出来,我还是写工厂农民好了。” 在离开中国的这些年里,何伟一直保证会回到中国,但这个计划可能还要拖上好几年。“我们真的会回来。我还想在中国写东西,我们不再年轻,我可以在埃及、在中国工作,这可能比在美国工作更为重要。我学过汉语,有中国经验,可不能浪费,而且在中国还有很多机会。此外也有些私人原因,我们都比较喜欢中国,在这里生活很开心。我们的两个小孩,95%像中国人,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外国人。这是好事情,我不要她们像我。我们会要求她们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历史。我们希望将来能住在中国内地,但也有很多麻烦问题,比如教育,我不希望女儿们去那种外国学校,很贵,没有必要浪费钱。” 但下一次回到中国会以什么样的身份?“我们都不知道,没有做决定。” (:王谦)
先声药业研发西宁专治白癜风的医院长沙治疗白癜风医院
- 上一篇: 藩国网间心事
- 下一篇 藩国是谁推了她一把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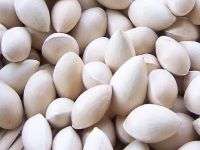
-
湖南3年办10个高研班培训中医人才
2019-07-13

-
国医大师石学敏河南郏县作专题讲座
2019-07-12

-
经常吃核桃可健脑益智
2019-07-11

-
端午临近话艾浴
2019-07-07

-
中国中医科学院课题组赴韩交流
2019-07-07

-
七里香药用验方
2019-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