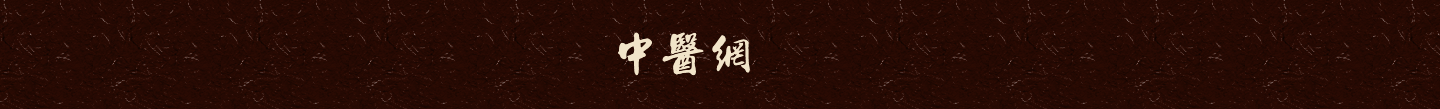藩国废名小说文章之美htt
中药养生 2020年07月23日 浏览:6 次
吴晓东:废名小说“文章之美” 《扬子江评论》吴晓东 19 2年12月,开明书店出版了废名的别开生面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在该书末页的广告中,为同样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废名短篇小说集《桃园》、《枣》,长篇小说《桥》,连同《莫须有先生传》四个单行本统一做了一个广告。广告语用的是周作人对于废名的评论:
我觉得废名君的著作在现代中国小说界有他的独特的价值者,其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
文艺之美,据我想形式与内容要各占一半,近来创作不大讲究文章,也是新文学的一个缺陷。的确,文坛上也有做得流畅或华丽的文章的小说家,但废名君那样简錬的却很不多见。
开明书店这一广告策略不能不说足够聪明。作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废名的所有小说的单行本都由周作人写序或跋,亦可见周作人对这一弟子的看重。附于《莫须有先生传》书末这一广告语中的前一段即引自周作人为《枣》与《桥》写的序言,后一段则出自《桃园》跋。
广告所择取的这两段文字中,周作人都对 文章 的范畴予以强调。而通观周作人对废名创作的评论,可以看出,对 文章 的重视的确是周作人一以贯之的文学主张,譬如在写于194 年的《怀废名》一文中,周作人引用自己19 8年的文字: (废名)所写文章甚妙 《莫须有先生传》与《桥》皆是,只是不易读耳。 [1]周作人把 不大讲究文章 ,视为 新文学的一个缺陷 ,这可能是周作人格外看重废名的文章的原因所在。周作人也曾选择从文章的角度来读废名从1925年即在报刊上连载并于19 2年出版第一卷单行本的长篇小说《桥》,以至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时也选了《桥》的六章,分别为《洲》、《万寿宫》、《芭茅》、《 送路灯 》、《碑》、《茶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 散文一集》导言中周作人这样说明理由: 废名所作本来是小说,但是我看这可以当小品散文读,不,不但是可以,或者这样更觉得有意味亦未可知。 这种 意味 ,大概主要来自于 文章之美 。而借助于周作人 文章之美 的眼光,读者或许可以看出《桥》的一些精义之所在,也或许更能准确定位废名的《桥》以及废名小说文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有论者称废名是 文章家 中最肆力于文章者 ,并称《桥》和《莫须有先生传》的 文字的别致,艰涩,差不多达到了叫人不敢相信的程度,在新文学的创作中,不愧为别树一帜的作品 [2]。
在1925年写的《桃园》跋中,周作人引述了废名的《桃园》中的一段文字:
铁里渣在学园公寓门口买花生米吃!
程厚坤回家。
达材想了一想,去送厚坤? 已经走到了门口。地铁站台内等四五趟车还是挤不上去的“战役”每天都在上演。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达材如入五里雾中,手足无所措, 当然只有望着厚坤喊。
周作人称: 这是很特别的,简洁而有力的写法,虽然有时候会被人说是晦涩。这种文体于小说描写是否唯一适宜我也不能说,但在我的喜含蓄的古典趣味(又是趣味!)上觉得这是一种很有意味的文章。 [ ]周作人肯定废名的是 简洁而有力的写法 ,从自己 喜含蓄的古典趣味 出发读出了废名 文章 的别有意味。
如果说在这篇《桃园》跋中,周作人对废名的小说文体还有些拿不准, 晦涩 的评价还有些负面,那么到了为《枣》与《桥》写的序中,周作人则借助对晦涩的深入讨论明确表达了对废名文章之美的赞赏: 我读过废名君这些小说所未忘记的是这里面的文章。如有人批评我说是买椟还珠,我也可以承认,聊以息事宁人,但是容我诚实地说,我觉得废名君的著作在现代中国小说界有他的独特的价值者,其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 周作人继而称:
从近来文体的变迁上着眼看去,更觉得有意义。废名君的文章近一二年来很被人称为晦涩。据友人在河北某女校询问学生的结果,废名君的文章是第一名的难懂,而第二名乃是平伯。本来晦涩的原因普通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我想现今所说的便是属于这一方面。在这里我不禁想起明季的竟陵派来。 公安派的流丽遂亦不得不继以竟陵派的奇僻,我们读三袁和谭元春刘侗的文章,时时感到这种消息,令人慨然。公安与竟陵同是反拟古的文学,形似相反而实相成 。民国的新文学差不多即是公安派复兴,唯其所吸收的外来影响不止佛教而为现代文明,故其变化较丰富,然其文学之以流丽取胜初无二致,至 其过在轻纤 ,盖亦同样地不能免焉。 简洁生辣的文章之兴起,正是当然的事。[4]
周作人也正是在 简洁生辣 的意义上评论俞平伯,在《燕知草》跋中,周作人认为: 我平常称平伯为近来的一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字意味的一种,这类文章在《燕知草》中特别地多。 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 [5]周作人的这种思路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说得更加清楚,称公安派的流弊在于 过于空疏浮滑,清楚而不深厚 , 于是竟陵派又起而加以补救 。 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 , 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 [6]。
周作人对废名文章的称许当然与他自己的文学理想有关。废名在某种意义上也实践了周作人的文学史方略。但是,周作人从竟陵派的文学资源上讨论废名的文章,或许只说出了《桥》的文体特征的一部分。《桥》的文学渊源和文体风格乃至诗学语言远为丰富而复杂,而《桥》的真正意义或许在于,它所汲取的文学养分其实是难以具体辨识的,已经为废名的创造性所化。
其实在1925年所写的《竹林的故事》序中,周作人即曾经赞赏过废名的 独立的精神 : 冯君从中外文学里涵养他的趣味,一面独自走他的路,这虽然寂寞一点,却是最确实的走法,我希望他这样可以走到比此刻的更是独殊地他自己的艺术之大道上去。 [7]这种对 自己的艺术之大道 的期许,可以说在废名的《桥》中大体上实现了。其实《桥》作为现代小说,的确内涵着丰富的 中外文学 的 涵养 ,其语言和思维也同时表现出西方文学的影响,这与废名读英文系,读莎士比亚、哈代和波德莱尔大有关系。但《桥》之所以是别开生面之作,主要表现在融会贯通的化境及其独创性方面。鹤西便称赞《桥》说: 一本小说而这样写,在我看来是一种创格。 [8]朱光潜把《桥》称为 破天荒 的作品:
它表面似有旧文章的气息,而中国以前实未曾有过这种文章。它丢开一切浮面的事态与粗浅的逻辑而直没入心灵深处,颇类似普鲁斯特与伍而夫夫人,而实在这些近代小说家对于废名先生到现在都还是陌生的。《桥》有所脱化而却无所依傍,它的体裁和风格都不愧为废名先生的特创。[9]
《桥》之所以是中国以前实未曾有过的文章,朱光潜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屏弃了传统小说中的故事逻辑, 实在并不是一部故事书 。当时的评论大都认为 读者从本书所得的印象,有时象读一首诗,有时象看一幅画,很少的时候觉得是在 听故事 。因此,如果为废名的小说追根溯源的话,废名可以说最终接续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几千年的诗之国度的诗性传统,他在小说中营造了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诗性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废名堪称是中国现代 诗化小说 的鼻祖,从废名开始,到沈从文梧桐私语_sissi:不管是谁代言、何其芳、冯至、汪曾祺,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能够梳理出一条连贯的诗化小说的线索。而废名作为诗化小说的 始作俑者 ,为现代小说提供了别人无法替代的 破天荒 的文体。在某种意义上说,废名的文体是融汇了古今中外的养分, 特创 出的一种文体。正像批评家刘西渭对废名的评价: 在现存的中国文艺作家里面 很少一位象他更是他自己的。 他真正在创造,遂乃具有强烈的个性,不和时代为伍,自有他永生的角落。成为少数人流连往返的桃源 [10]。这个让 少数人流连往返的桃源 ,就是废名所精心建构的诗意的小说世界。
这个诗意的小说世界从语言上说当然得益于废名的文章之美,而废名的文体的 涩味与简单味 也许的确与周作人追溯的竟陵派相关,但是就《桥》的文学语言的精髓而言,则或许是废名追慕六朝和晚唐的结果,就像废名后来自述的那样: 我写小说,乃很象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 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 [11]废名小说的诗化文体之精炼、浓缩,以及意境的空灵、深远,正得益于陶潜、庾信、李商隐的影响。如《桥》中的文字: 一匹白马,好天气,仰天打滚,草色青青。 可以说充满了跳跃、省略和空白,作为小说语言,其凝练和简捷,与六朝和晚唐诗境相比,实在不遑多让。而《桥》更擅长的,是意境的营造:
实在他自己也不知道站在那里看什么。过去的灵魂愈望愈渺茫,当前的两幅后影也随着带远了。很象一个梦境。颜色还是桥上的颜色。细竹一回头,非常惊异于这一面了, 桥下水流呜咽 ,仿佛立刻听见水响,望他而一笑。从此这桥就以中间为彼岸,细竹那里站住了,永瞻风采,一空倚傍。(《桥 桥》)
一个普通的生活情景,在废名笔下化为一个空灵的意境,充满诗情画意,有一种出世般的彼岸色彩。
《桥》作为一部 创格 的 破天荒的作品 ,它的特出之处还表现在废名对古典诗歌中的意象、典故、情境甚至是完整的诗句的移植。如: 琴子心里纳罕茶铺门口一棵大柳树,树下池塘生春草。 谢灵运的 池塘生春草 就这样直接进入废名的小说中,嫁接得极其自然,既凝练,又不隔,同时唤起了读者对遥远年代的古朴、宁静的田园风光的追溯和向往。又如:
就在今年的一个晚上,其时天下雪,读唐人绝句,读到白居易的《木兰花》, 从此时时春梦里,应添一树女郎花 ,忽然忆得昨夜做了一梦,梦见老儿铺的这一口塘!依然是欲言无语,虽则明明的一塘春水绿。大概是她的意思与诗不一样,她是冬夜做的梦。(《茶铺》)
这一繁复的语境也是从唐人绝句中衍生出的,梦中 老儿铺 的一塘春水绿,与白居易的诗句互相映衬,诗性意味便更加浓郁。可以看出,古典诗句和典故在小说中经过废名的活用,具有了某种诗学的功能。它不再是独立存在的意象与意境,而是参与了叙述和细节构建,所谓 字与字,句与句,互相生长 [12]。废名正是由古典诗词中的意境引发小说中虚拟性联想性的情境,从而使传统意味、意绪、意境在现代语境中衍生、生长和创生,传统因此得以具体地生成于现代文本中。在这个意义上说,《桥》是中国文学以及文化中 诗性的传统 或 传统的诗性 的具体体现,传统存留于废名的诗性想像中,也存留于废名对晚唐和六朝诗意的缅想之中。
周作人把废名的晦涩主要归于文体问题,但《桥》之所以晦涩恐怕更与废名试图处理的是意念和心象有更直接的关系。《桥》营造与组织了大量的意念与心象,套用废名在《桥》中的表述,《桥》乃是一部 存乎意象间 的作品(《天井》)。有相当多的心象体现了废名个人化的特征, 晦涩 与这种 个人化 有着更直接的关系。《桥》中富有表现力的部分正是其中濡染了作家自己的个人化色彩的意念:
走到一处,夥颐,映山红围了她们笑,挡住她们的脚。两个古怪字样冲上琴子的唇边 下雨!大概是关于花上太阳之盛没有动词。不容思索之间未造成功而已忘记了。(《花红山》)
在琴子看来,花上太阳之盛的情状没有动词可来形容,只好暂时借用了 下雨 ,这在人们所习惯了的 下雨 的既有意义之外赋予了它新奇的意义,其中关涉了语言发生学的问题。下雨本身并不古怪, 古怪 的是废名赋予 下雨 以 花上太阳之盛 的意思,这显然是作者个人化的意念,没有公共性和通约性。这里关键问题尚不在于 下雨 与 花上太阳之盛 是否有内在的相似性,而在于废名试图藉此激发汉语的新的表现力。又如:
春女思。
琴子也低眼看她,微笑而这一句。
你这是哪里来到一句话?我不晓得。我只晓得有女怀春。
你总是乱七八糟的!
不是的, 我是一口把说出来了,这句话我总是照我自己的注解。
你的注解怎么样?
我总是断章取义,把春字当了这个春天,与秋天冬天相对,怀是所
以怀抱之。 (《花红山》)
这固然有废名的笔墨趣味在里面,但并不是一种文字游戏,细竹自己的 注解 与 断章取义 反映了废名在现代语境下对重新激活传统语言的刻意追求,其中包含废名对语言的陌生化观照,对媒介的自觉,对语言限度的体认。在《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一文中,废名认为 文字这件事情,化腐臭为神奇,是在乎豪杰之士 ,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尤其体现在复活古典文学所惯用的比喻之中。有研究者指出: 使 死 的或者 背景的 隐喻复生是诗人的艺术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1 ]废名在激活了古典文本中程式化了的隐喻的同时,也就突破了对语言传统的惯常记忆,使古典词语在新的意指环境中复活。他对古诗的引用,对典故的运用,都是在现代汉语开始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环境中思考怎样吸纳传统诗学的具体途径。他对古典诗歌的理解也是把古典意境重新纳入现代文本使之获得新的生命。虽然《桥》常常移植古典的诗文意境,但往往经过了自己的个人化改造,并纳入自己的文本语境之中。
北方骆驼成群,同我们这里牛一般多。
这是一句话,只替他画了一只骆驼的轮廓,青青河畔草,骆驼大踏步
走,小林远远站着仰望不已。(《树》)
一句 青青河畔草 被纳入小林的一个想象性的情境之中,在与 骆驼大踏步走 的组合中获得了废名的个人性,小林所仰望着的这一其实是他虚拟的情境,被 青青河畔草,骆驼大踏步走 的组合提升了。《桥》中不断地表现出废名对古典诗歌的充满个人情趣的领悟。如《桥》一章: 李义山咏牡丹诗有两句我很喜欢, 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 你想,红花绿叶,其实在夜里都布置好了, 朝云一刹那见。 琴子称许说 也只有牡丹恰称这个意,可以大笔一写 。在《梨花白》一章中,废名这样品评 黄莺弄不足,含入未央宫 : 一座大建筑,写这么一个花瓣,很称他的意。 这也是颇具个人化特征的诠释。鹤西甚至称 黄莺弄不足 中的一个 弄 字可以概括《桥》的全章。 弄 字恐怕正表现了废名对语言文字个人化的表现力的玩味与打磨。鹤西称《桥》是一种 创格 ,也正是指废名在诗化的语言和意境方面的个人化的创造[14]。
[1]药堂(周作人):《怀废名》,冯文炳(废名),《谈新诗 附录》,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
[2]《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中国文艺年鉴社,《中国文艺年鉴(19 2年)》,现代书局19 年版,第28页,
[ ]周作人:《跋》,废名,《桃园》,开明书店19 0年版。
[4]周作人:《栆和桥的序》,废名,《桥》,开明书店19 2年版,第 5页。
[5]周作人:《燕知草跋》,俞平伯,《燕知草》,北新书局1929年版。
[6]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人文书店19 4年版,第51 52页。
[7]周作人:《竹林的故事序》,冯文炳(废名),《竹林的故事》,北新书局1925年版,第 页。
[8]鹤西:《谈〈桥〉与〈莫须有先生传〉》,《文学杂志》19 7年第1卷第4期。
[9]孟实:《桥》,《文学杂志》19 7年第1卷第 期。
[10]刘西渭:《〈画梦录〉 何其芳先生作》,郭宏安编,《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 2页。
[11]废名:《废名小说选 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12]废名:《说梦》,《语丝》1927年第1 期。
[1 ](英)泰伦斯 霍克斯:《隐喻》,穆南译,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 5页。
[14]参见吴晓东:《废名 桥》,上海书店2011年版。
内蒙古治疗白斑的医院脑动脉硬化吃什么药好烟台男科医院哪家好
- 上一篇: 藩国巧克力在中国的历史最早因无药效被康熙嫌弃
- 下一篇 藩国爱因斯坦给我们的十个宝贵建议

-
刮痧缓解身体气不顺
2019-07-12

-
感冒不想打针试试中医食疗
2019-07-12

-
蜈蚣旗根的功效与作用
2019-07-06

-
镜面草的功效与作用
2019-07-06

-
北京中医药大学创作的舞蹈诗岐黄志亮相法国
2019-07-06

-
金老梅叶的功效与作用
2019-07-02